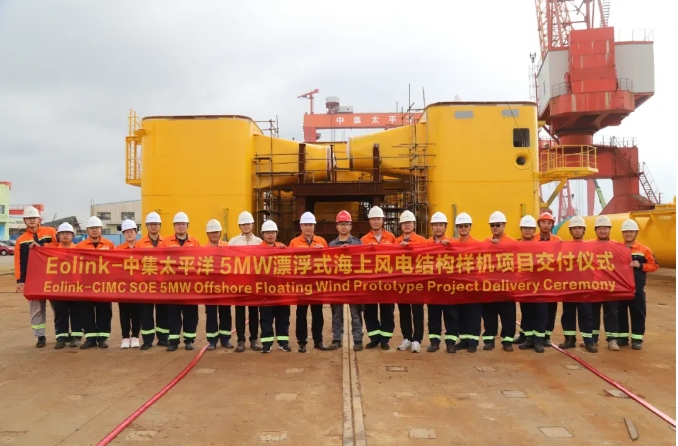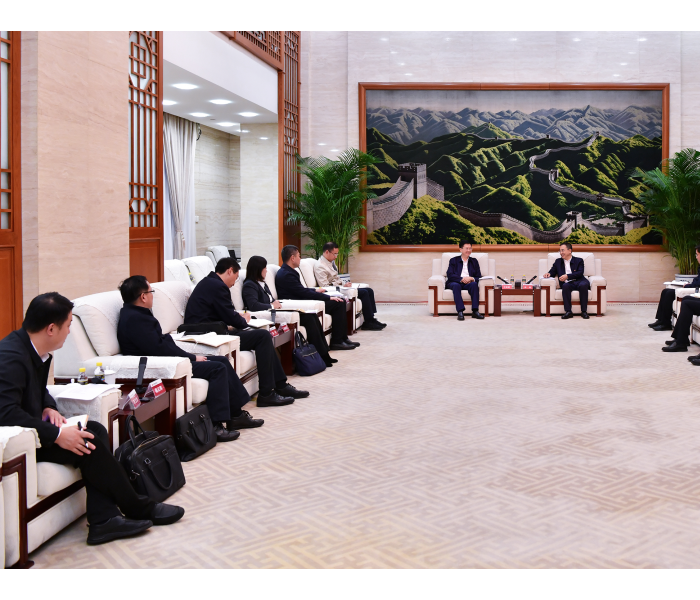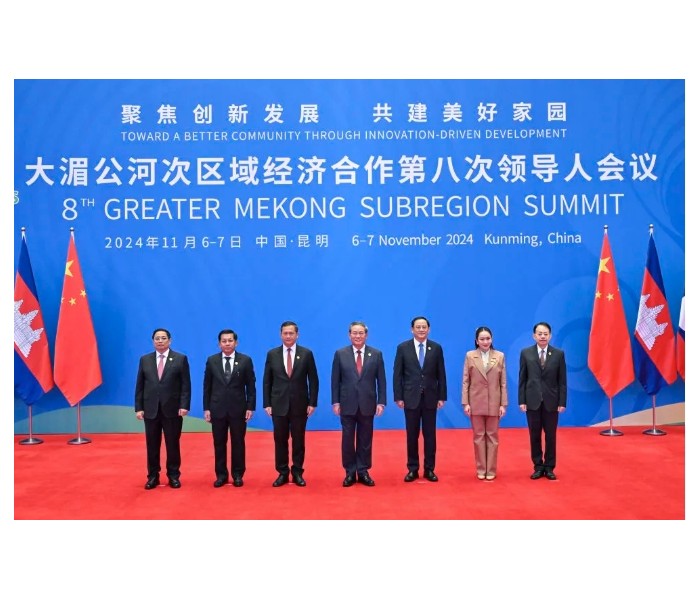8月18日,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自7月16日碳市场启动以来,全国碳市场运行平稳,在第一个履约周期,全国燃煤发电行业2162家企业被纳入碳市场的范围,碳市场共覆盖45亿吨二氧化碳排放量,交易价格从首日开盘价的每吨48元上升到8月17日收盘价每吨51.76元。开市一个月来,全国碳市场排放配额累计成交量达702万吨,累计成交额3.55亿元。
据介绍,下一步生态环境部还将推动《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尽快出台,修订完善相关的配套制度和技术规范体系,完善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机制。同时强化市场管理,加强碳排放数据的质量管理,强化相关制度的执行落实,加强对全国碳市场各个环节的监管,有效防范市场风险。
在此之前,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要求坚持全国一盘棋,纠正运动式“减碳”,先立后破,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过程中,我国还存在哪些挑战和风险?下一步应如何推进?就此,记者杂志、经济网记者采访了国合洲际能源咨询院院长王进。
记者:对于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纠正的运动式“减碳”,您认为产生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王进:自“双碳”目标提出以来,各地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偏差,部分地区将“减碳”视为短期内必须优先完成的政治任务,用力过猛。
具体来看,能源规划中有一项特别重要的内容,就是能耗总量的指标分解。控制能耗总量主要依靠行政手段,从省里到市里,从市里到区县,直至具体到企业,摊指标、下任务,层层下压,谁超额,谁当责。反过来,下面为保证任务完成,不得不层层加码执行力度,甚至采用“一刀切”的懒政,直接限制。合法合规经营的企业被迫停工限产,新增投资迟迟无法落地,导致一些经济相对发达地区拉闸限电。另外,一些采煤地区不顾市场情况,“一窝蜂”式限制甚至关停煤矿生产,引发煤炭市场供应紧张,继而引发煤炭等大宗商品供需失衡,价格飙涨,“限电令”不得不重启,对经济发展及居民生活都造成了不良影响。
推进“双碳”工作是一项系统性、长期性的任务,不能孤立对待。首先要明确我国当前发展的主要目标是什么,为完成“双碳”目标而开展运动式“减碳”,一旦影响其他优先目标的达成,可谓本末倒置,得不偿失。
记者:在您看来,哪些发展目标应该优先于“双碳”目标?
王进: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主要预期目标很有参考价值:国内生产总值增长6%以上;城镇新增就业1100万人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5.5%左右;居民消费价格涨幅3%左右;进出口量稳质升,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居民收入稳步增长;生态环境质量进一步改善,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3%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量继续下降;粮食产量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其主要涉及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居民就业、物价水平、居民收入)、外贸稳定、生态环境及粮食能源安全等目标。显然,这些目标的优先级都在“减碳”之上。
政府工作报告多次强调,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就国家而言,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一旦经济增长停滞,不仅产业转型升级失去动力,止步于发达国家门槛前,现有市场份额也将被其他国家蚕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地方而言,虽然不再“唯GDP论”,但民生改善、社会保障、文化建设乃至生态文明建设,都离不开经济发展的支撑。现阶段,我国碳排放与经济发展尚未脱钩,存在紧密的正相关关系,人为限制碳排放增量,将直接抑制经济增长,同时也会限制我国节能减碳技术和产业的发展。摆正碳排放的位置,当节能减碳技术和管理水平大幅提升时,经济发展不但不会受到抑制,反而会更具效率,更有比较优势。
记者:6月份,浙江率先出台了《浙江省碳达峰碳中和科技创新行动方案》,明确提出到2025年如期实现碳达峰,2030年高质量实现碳中和,并据此制定了相应的技术路线图和行动计划。在您看来,地方政府在制定“双碳”规划时,应如何统筹全局?注意和避免哪些问题?
王进:“双碳”目标并不是要求每个地区、每个行业乃至每个企业都要在规定的时点实现,但浙江等部分地区抢先表态,一些企业率先明确时点,殊为难得。
2020年,浙江GDP为64613亿元,常驻人口6457万人,用电量为4830亿千瓦时,其规模已经超过欧洲的大部分国家。欧洲各国特别是几个大国的碳中和时间都设定在2045-2050年间,相比较而言,浙江的方案比较超前,意图通过全面系统的低碳、零碳和负碳技术实现攻关、创新、推广和广泛应用,在可再生能源、储能、氢能,特别是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等方面,率先取得重大突破。
与此同时,还有一些问题需要持续关注,例如,未来10年浙江能源需求量预估,逐年的低碳能源替代比例、来源与成本,CCUS逐年数量、比例和成本;如果10年间技术突破低于甚至远低于预期有何替代办法;当经济发展及保障民生等与“双碳”目标发生冲突时,如何排序和取舍等,都应该有相应的预案。
由此也可以总结出,各地在制定“双碳”规划时,要以科学论证为基础,首要考虑的是当地是否拥有低碳资源,抛开资源谈能源低碳转型就是纸上谈兵。以当前最成熟、占比最高的低碳能源水电为例,我国水力资源主要集中在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澜沧江、乌江、长江上游、南盘江、红水河、黄河上游、湘西、闽浙赣、东北、黄河北干流以及怒江等流域,西南与华南地区水力发电总量占比超过四分之三,而三北地区(东北、华北和西北)不具备大规模开发水电的条件。每个地方都发展可再生能源是不可行的,投入产出比相差甚远,东部省份人口稠密,土地成本高昂,分布式可再生能源也不能承担主要供给责任。资源是有限的,运费也需要考虑。
其次,还要考虑低碳能源替代的现实可行性。如果本地区确有一定数量的低碳能源资源,那么这些资源是否能被高效开发出来,需要多少资本,何种技术,多长时间,能否平稳对接并替代高碳能源的有序退出?这些都需要仔细测算和规划。反之,如果本地没有足够的或者几乎没有低碳能源资源,必须从外地区甚至国外引进,那么不确定因素将会增加,经济性会更加不可控。过去,我国一些地区强制推行过冬季供暖“煤改电”和“煤改气”,几乎是“一窝蜂”、“一刀切”,又恰巧碰到气源紧张,气价暴涨,电力供应不足,不少地方受到严重影响。
推进“双碳”目标,不管是本地供给还是区域外购入,安全性和经济性是否得到保障是基本前提。具体的判断依据是,低碳能源的替代是否能保证终端用能充足,而且总体成本不高于现有价格。
记者:在低碳转型的过程中,应如何保障能源的安全性和经济性?
王进:首先,与碳税类似,抓住能源供给端“减碳”是方向性错误,在消费端减少碳排放更加合理。国内的煤炭企业也好,油气企业也好,首要任务应是保证供给,我国《“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就明确提出,到“十四五”末期,我国能源综合生产能力要超过46亿吨标准煤,能源低碳转型必须在确保能源安全的前提下进行。
其次,从能源安全角度出发,需求侧的低碳转型也应分轻重缓急。受资源禀赋限制,煤炭虽然是一次能源中的高碳品种,但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是我国保证国家能源安全的现实选择。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能源体系还在建设中,碰到的困难和障碍比较多,短期内我国还无法承受同时“削煤去油”的后果,考虑到石油对外依存度较高,交通电气化可以排在前列。
就经济性而言,供给得不到保证,价格必受影响,仅靠行政手段限制终端能源价格不是长久之计,只有适当放开能源资源开发和投资的限制,经济性才能得以保证。
对可再生能源而言,目前水电有比较优势,开发比例也是最高的。虽然光伏和风电的平价项目也逐渐成为主流,但其对电网平衡调节要求较高,还需要配备一定的储能,电网系统需要全面改造和升级来适应高比例的可再生能源,这些支出将推高终端用能成本。未来,随着电网数字化升级、智慧化水平提高,供求两端及时响应能力的提升,电力交易成本下降,风光等可再生能源在终端用能的安全性和成本等方面将取得重大突破,超越传统的高碳能源,那时,大规模的替代才切实可行。